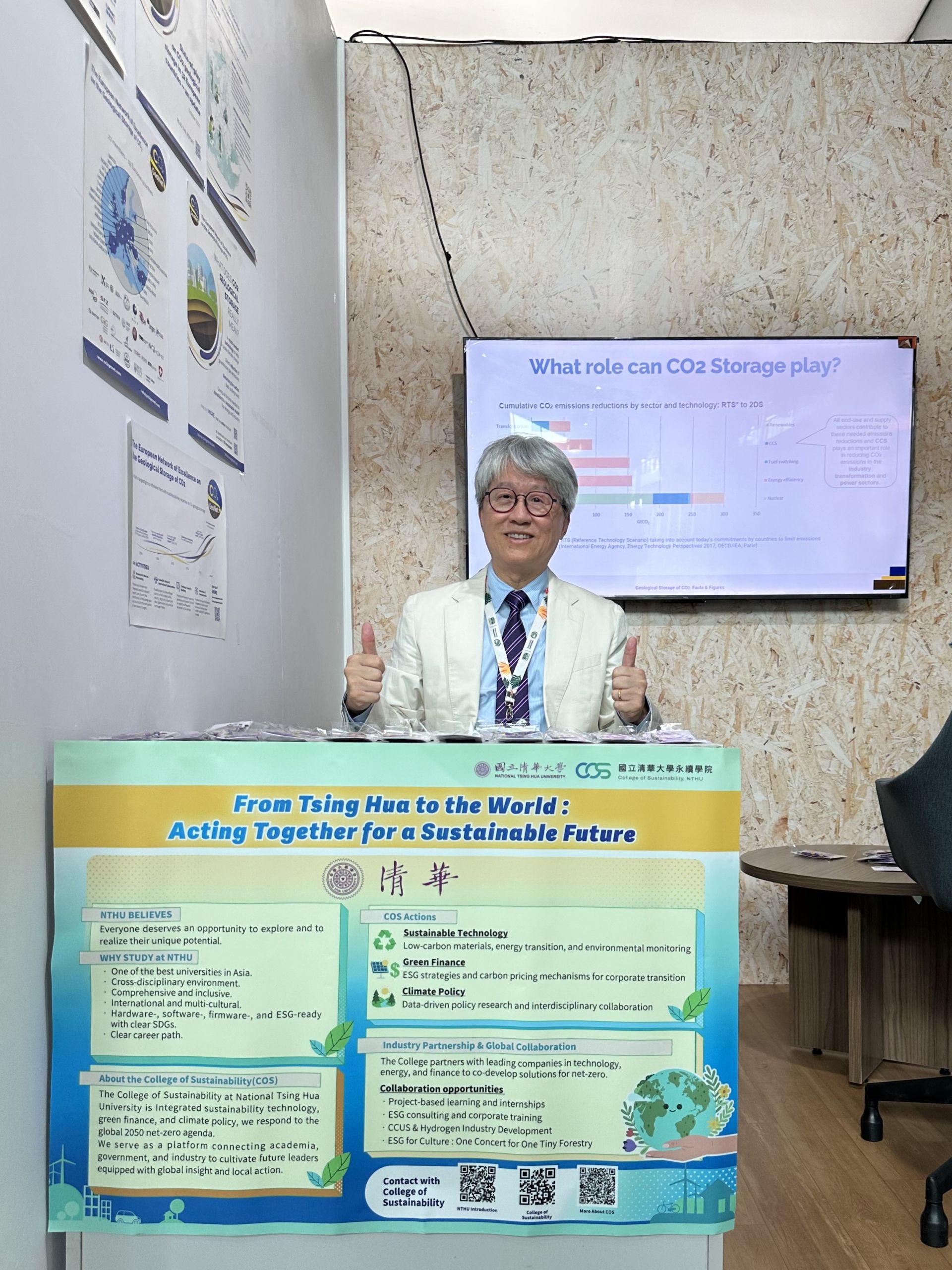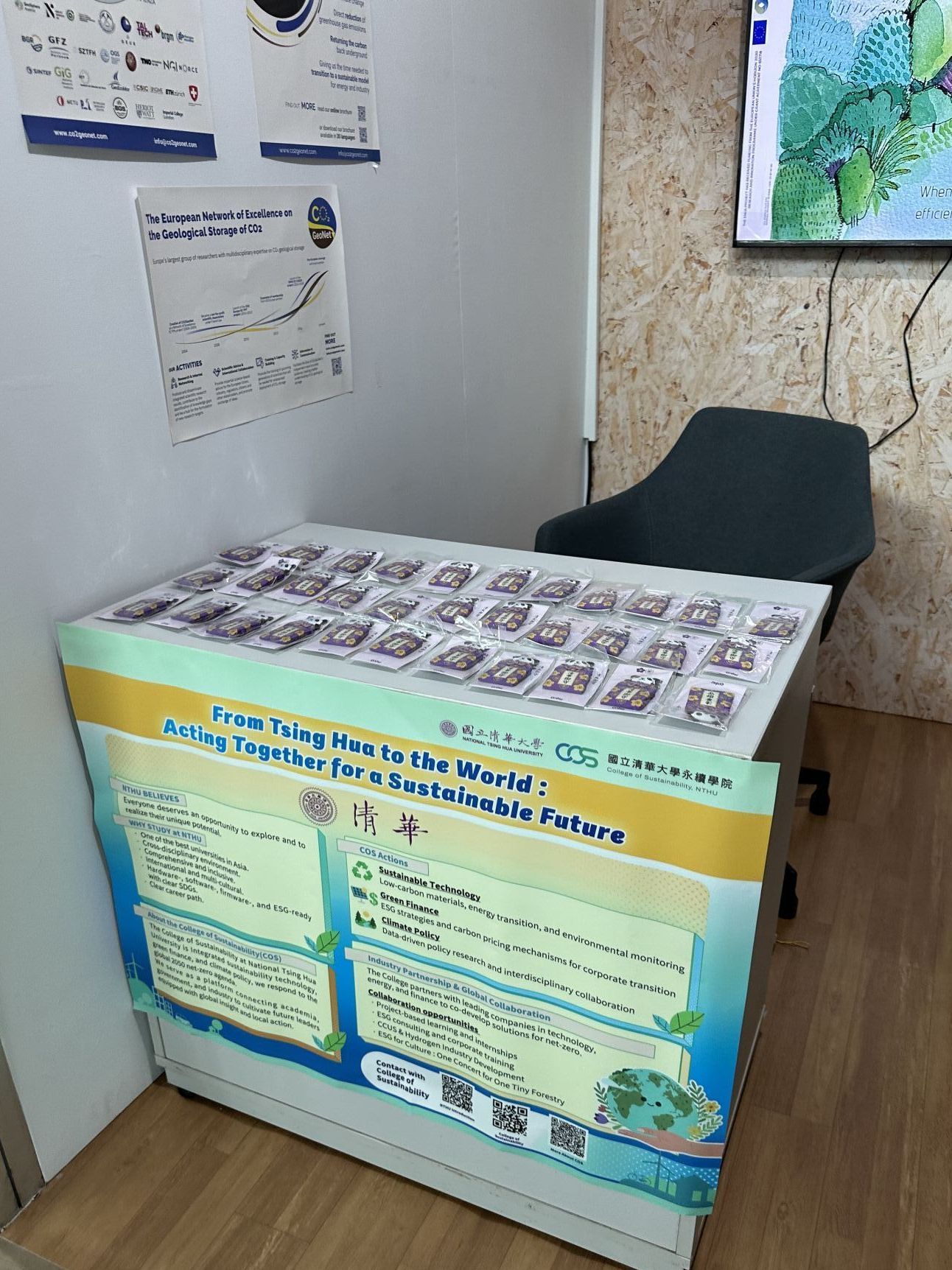2025. 11.17|范建得|巴西貝倫市(Belém)
(接續前篇報導:https://cos.nthu.edu.tw/news-20.html)
台灣該怎麼看待CCPI的再次差評?我們是否也該開始為明年爭扎於結構性限制偏見下的光電三法負面效應憂心?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台灣在評比中分數低,不完全是表現差,而是「結構性不利」:CCPI 採用全球一致的產地排放(territorial emissions)、每人能源使用、再生能源占比與 2030 目標去比較,然而台灣在以下結構上天生劣勢:
1. 出口導向的工業型經濟導致人均排放與能源使用量被放大:
簡言之,生產端排放全算在台灣頭上,但大量產品卻是供應全球消費。加上產業能源需求高,也使得人忪均能源使用和每人的排放量,都在國際評比中偏高。簡單的說,在CCPI的方法裡我們是吃虧的,且責任是大家必須一體承受的。
2. 能源高度仰賴進口、缺乏自主化石燃料:
無充足的在地天然氣、石油、煤礦,也無大水力或大面積地面風場。其次,再生能源起步盼晚,難度也比北歐、澳洲、美國等國高得多。簡言之,再生能源占比基期低,分數自然也低。
3. 島國地理、土地有限:
台灣地狹人稠、敏感環境區多、人口密度高。相對的導致光電、風電、儲能、輸電線路的可用空間受限。從而在以「占比」和「2030目標」為核心評比架構下自然處於劣勢。如今新通過的光電三法,恐怕會進一步深化這個失分的弱點。
4. 無法正常參與UNFCCC與COP嚴重影響國際氣候政策分項
CCPI的一大評分項目是「國際氣候政策」占評分20%。台灣因國際地位受限,無法於UNFCCC場域展現角色,無論實際努力多大,這項分數幾乎不可能高。面對這種結構性壓低總分的現況,若台灣還不能積極投入唯一透過市場機制可創設的連結,未來恐很難見到台灣善用國際公約機制來彰顯國際氣候政策表現的機會。
其次,剛剛通過的光電三法(2024–2025),恐怕也會成為「再生能源負面評價」的新來源。
雖然本年度CCPI尚未完全反映光電三法通過的後續發展,但其負面趨勢恐將被未來專家評分納入歡法政風險考量。具體包括:
1. 光電退場潮與投資不確定性:
地面型光電在農地、山坡地、水域的使用範圍將更進一步的被限制。此外,主要開發模式限縮,開發成本上升,或許將導致許多案場擱置或撤件。近年來,有些國際觀察家已經指出台灣能源政策搖擺、投資環境不穩,有可能拖慢增速。如今這個法制面向的發展是否雪上加霜,值得深思。
2. RE 2030 目標更難達成:
按,台灣本已因土地限制而難以快速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光電三法恐怕會使太陽能新增量提前「踩剎車」。這種現象是否在CCPI的「2030 再生能源目標可信度」項目上會獲得較低評分,同樣值得斟酌。
3. 政策一致性受到質疑:
既有案場合法性與轉換標準突然變動,勢將引起國際投資機構(如 ESG 投資人)、綠電買家、RE100 企業的疑慮。這種可能顯然會在CCPI的「國家氣候政策評分(專家評價)中被扣分。
4. 對輸電與儲能佈局的連鎖效應:
光電的量縮也同時代表2030前電網投資報酬、規劃方向不明,這是否?會使台灣電力轉型的可信度受國際質疑,實在不容忽視。因為,這會是國際評分視為能源轉型「整體策略不清晰」的判斷基礎。
綜上結論:低分不等於台灣表現差,而是評比分母與結構不同,但持續的法政措施負面效應,卻是我們應知所趨避的地方
簡而言之:CCPI的指標方法本身就不利於出口型、能源島國、無法加入 UNFCCC的經濟體,在方法上,我們唯有繼續提升減碳強度並加強能源結構的轉型,尤其在住商交通部分的努力,來提升人均排放和能源使用效率的績效,才有可能在這種不利的評估架構上有所突破。準此,當前光電三法又在關鍵的「再生能源占比」與「政策可信度」兩大分項上新增負面壓力,我們勢必要審慎以對,以免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沼。
此外,我們要相信,這個評比並不代表台灣「沒有進步」,而是在 CCPI 這個評比架構中,台灣的起跑點與後續政策走向確實被放大了其中的劣勢部分,若我們希望在此架構下改善評分,必須重新檢視2030減碳與再生能源目標(提高企圖心)、調整或補正光電三法可能造成的投資與增量停滯問題。其次,穩定且一致地推動能源政策,以提升「政策可信度」的專家評分,顯然也是當豫務之急。